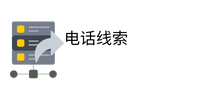映射
蒂姆·科尔:我很高兴亨利重提他在上一篇博文中顺便提到的一点:有以及说什么时的反思,因为这对于理解究竟说了什么(以及没说什么)至关重要。正如亨利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意识到,幸存者的讲述可能涉及“口述心理学”、“口述哲学”、“口述神学”或“口述叙事学”,而不仅仅是“口述历史”。他提醒我们,个人选择复述的原因多种多样,这一点很重要。思考创作资料来源的原因是我们在历史方法课上学到的第一课。然而,正如亨利所说,由于这 手机号码数据 类元数据的缺失,在大多数大型口述历史项目中,获取这些原因往往很困难。亨利对同一位幸存者进行多次采访的做法,正是培养这种更广泛的语境理解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法是认真聆听采访本身以及在复述过程中这些反思确实出现的时候,或者尽可能广泛地借鉴某个幸存者的采访和文字。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大屠杀风景》中,我试图做到这两点。例如,在几个章节中,我引用了对大卫·伯格曼的两次采访,他是我在OHR文章中提到的幸存者之一。这些采访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观看和聆听大卫早期制作的视听演
示很有价值这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他如何以及为何决定将他的战时故事构思成一系列火车旅行。
尽管正如亨利所说,有些学者正在围绕口述历史和大屠杀开展重要的新工作,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大屠杀研究——包括史学和文献收集——往往落后于口述历史的发展。我想更进一步。我的感觉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屠杀研究时期仍然是一个极其保守的分支领域,并且由于概念和方法论的保守主义倾向而显得较为贫乏。
近二十年来,我关于大屠杀的大部分研究都呼吁人们思考事件的空间性。随着我开始更多地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我开始有意将这一呼吁扩展到口述历史学家。正如我们在博客上的对话所暗示的那样,空间和地点在口述历史中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在“空间转向”之后,对口述历史的思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在亨利列出的关于个人复述故事时发生的事情的类别中再添加一个类别。除了“口述心理学”、“口述哲学”、“口述神学”、“口述叙事学”和“口述历史”之外,我还想添加“口述地理学”。我并不觉得自己对“口述地理学”的含义有任何全面的理解,而只是预感,从空间角度思考访谈过程和成果的各个方面可能很有价值。这样做并非仅仅为了追赶又一波学 行为或不作为阻碍了协议 术潮流和时尚。相反,它受到这样一种感觉的驱动:认真对待地点和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别人说了什么、他们如何说以及他们为什么说。
尾声:“生存与毁灭
亨利·格林斯潘:本周,我们班讨论了我对鲁本的采访。鲁本是一位幸存者,我第一次和他交 新加坡电话列表 谈是在1976年。在我认识的所有幸存者中,鲁本的崩溃最为明显。我十年的临床心理学家工作经验并没有让我做好面对像他这样深刻的抑郁的准备。他把必要探究幸存者在选 自己描述成一个“吉尔古尔”(gilgul)——意第绪语,意为“迷失的灵魂”。鲁本说,吉尔古尔“既不属于旧世界,也不属于新世界。他只是四处游荡。他迷失了,你知道的。他迷失了。”鲁本所了解的欧洲犹太文化是一个“灭绝的物种”,“被连根拔起”,“彻底消失了”。鲁本作为残余继续生活,无处安身。事实上,虽然他的家位于一个中下阶层郊区,但他在底特律一个在1967年“骚乱”中被烧毁的地区拥有一家小型电器配件店。这些遗迹让他想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他在罗兹的犹太区。他写道:“一切都被木板封住了,一片狼藉。这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很像。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很像。” 鲁本就这样在底特律的犹太区找到了罗兹犹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