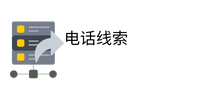这是他的遗言。一种相当进步的文明愿景,旨在治愈仇恨和毁灭的冲动 明与战争 。快乐的乐观主义——1932 年,即希特勒掌权的前一年,的奇怪乐观主义——当人们开始认为死亡驱力可以被吸收到文化中时。他认为,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与战争相悖——然而,1914年的战争在这方面标志着历史的重大突破,技术的巨大发展使这场战争成为第一场以暴力死亡为主要死亡原因的冲突。然而,就在三年前,即1929年,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弗洛伊德并没有表现出如此平静的心态,他对文明的平和美德的信念也不那么坚定。他似乎对死亡驱力是否可以教育抱有严重的怀疑 [3]。
现在俄罗斯人已经发起了一项教育活动。随着大炮的射击。他们极力捍卫自己正在进行文明战争的观点。它设想了军刀与洒水器之间新的神圣同盟。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热情支持下,似乎已领导了一场真正的救赎运动。正如埃里克·劳伦特(Eric Laurent)最近在谈及齐奥朗时所指出的,“他对绝对力量的坚信使他宣布,随着俄罗斯政治权力的上升,俄罗斯将抛弃马克思主义,回归宗教”[4 ]。一千年前,非基督徒的基辅人来到第聂伯河接受洗礼。但拯救沐浴的时代已经结束,那时,受洗者应该在洗礼水流淌的情况下聆听天父的声音。父亲的声音变得嘶哑,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听不见;此外,在伊斯兰国为了荣耀真主而挥舞军刀,将异教徒的头颅砍下之后,神圣的俄罗斯决定站起来,纠正被致命快乐所感染的变态的西方。普京不是最近在2023年2月21日向俄罗斯联邦议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宣称:“他们不断攻击我们的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和我们国家的其他宗教组织。 […] 看看他们对自己人民做了什么:破坏家庭、文化和民族认同、变态和虐待儿童直至恋童癖,这些都被视为常态。”他指责西方对俄罗斯发动“文明战争”,并反过来宣称要对严重腐败和腐化堕落的文明进行文明救赎战争。
战争,伴随着步调一致的军
无疑一直都是阳刚秩序、天父秩序的体现。手持大锤指挥瓦格纳的叶 比利时电话号码库 夫根尼·普里戈津是这支乐团的预期领袖。当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 [5]中讲到“传统群体”时,他指的是教会和军队,是人类的群体,是秩序的群体。在武力展示和军事等级制度之间,常规战争是父权秩序的体现。
在入侵初期,普京总统曾多次表示,莫斯科的目标是“使乌克兰国家去纳粹化”。今天,一位俄罗斯著名歌手公开呼吁,不仅乌克兰,而且欧洲和整个西方都要摆脱“LGBT帝国”毒品的影响。在俄罗斯电视台,对同性恋、觉醒或变性问题的处理占据着过度、过分的地位,与这些主题在我们自己的辩论中的实际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正如 LCI 的一位记者前几天晚上总结的那样:俄罗斯真有男子气概!俄罗斯的军刀和东正教的圣水洒水器反对西方灾难性的道德转型,这种转型贬低了西方的男性气概,普京在 2 月 21 日的重大演讲中说:“牧师有义务祝福同性恋者之间 您需要了解的有关 Zoho 销售团队对话式 AI 的一切 的婚姻。”针对破坏我们文明的享乐行为的特殊军事行动。针对权威人物衰落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我们免受西方堕落、衰败和颓废的影响。
但如果战争既不反对文明,也不支持文明,那会怎样?如果战争只是“文明的阴暗面” [6],那又会怎样呢?2015 年,玛丽·海伦·布鲁斯 (Marie-Hélène Brousse) 曾这样称呼战争,而就在十年前,她用战争来检验精神分析学 [7] 。战争已将其阴暗的面容转向我们。这场战争正在注视着我们,我们有必要关注它。和少数明智的思想家、心理分析家、不安的临床医生一样,他们也无法回避这样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即重新反思这个时代的现实,这个现实扭曲并重塑了这个时代。
因此当前的问题实际上可能就是保罗
·瓦莱里关于文明死亡率的问题 [8]。她不是。因为真理——沃尔特·本雅明在历史的弊病中看到了这一点——是,正如 M.-H.布鲁斯从根本上认为,战争不仅仅是文明的灾难性面孔,它会在今天投下可怕的阴影,战争本身就是文明。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想法——“他的‘野蛮’就是文明本身” [9]。换句话说,战争绝不意味着文明的消亡。相反,它会警告政治的变幻莫测。
“潜意识就是政治”:拉康的这个公式,雅克-阿兰·米勒和克里斯蒂安·阿尔伯蒂都曾 WhatsApp 号码 对此进行过强烈的评论,它认为潜意识不仅是“跨个体的”,它超越了我们小故事中狭隘的亲密范围,很大程度上溢出了沙发,甚至超越了分析办公室的墙壁,而且它与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历史产生共鸣并震撼了它,这证明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在这里关注乌克兰战争是合理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认为,精神分析对于“他者”一词有所论述,而这在先验上与精神分析无关。拉康将这一维度称为“外部时间”,即来自内部的陌生人的维度,同时,它导致将无意识从亲密关系中抽离出来,注入城市。这就是战争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