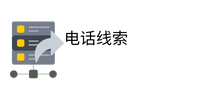“为什么要战争? » 弗洛伊德和拉康在这一点上存在分歧。在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于 1932 年合写的本书中,和平主义是文明人的合理立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对它(战争)感到愤慨,对于我们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宪法上的不宽容” [1]。弗洛伊德以一个痛苦的问题结束了他的文章。他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和平主义者。 “我们还要等多久其他人才能成为和平主义者? » [2]。
生命政治的局限性
拉康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真实现象保持距离:“它如此拒绝科学,这太疯狂了! […]但它仍然存在。也就是战争。他们都在那里,所有学者都在绞尽脑汁:战争 ? […] 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为此共同努力。 “这对他们不利” [3]。拉康则认为战争是权力的一个不可消除的维度。 “权力……每二十年需要一场战争。 […]这次他做不到,但无论如何他都会做到的” [4]。因此,人们认识到战争的必要性,认为战争是不会停止的,根据福柯的说法,战争给生命政治提供了一个限度。和平与生物政治措施并不适合所有人。通常,一个政权,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都会让其统治者想起自己的美好回忆,并引发战争。
帝国与暴君的力量
在关于战争及其原因的问题上,齐奥朗与拉康的观点一致。战争 与权力密不可分。在我们正在阅读的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文章中,齐奥朗严厉谴责了让这种事情在布达佩斯发生的西方民主国家,但除此之外,他还以科幻小说的口吻分析了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它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其暴政形式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实行君主制或“人民小父”的“人民民主”。最重要的是,这个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一项使命,首先就是通过成为“第三罗马”来拯救天主教基督教。 1917 年的俄国革命重新确立了孕育新苏维埃人和欧洲未来 保加利亚电话号码库 的使命。与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的前景和西方民主的胜利截然不同,齐奥朗宣称暴政的不可削弱性及其对人类施加的黑暗魅力。在大量矛盾的修辞法和惊人的公式中,他揭示了绝对权力的模糊清晰度以及它如何锚定在每个人的个人主观性中。像弗洛伊德一样,他认为暴君是一种内在的可能性,而不是政治上的异常现象。
“伊凡雷帝(其中最令人着迷的一位)把他的统治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他的国家变成了噩梦的典范,一个活生生、取之不尽的幻觉的原型,一个蒙古和拜占庭的混合体,集可汗和巴西勒斯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是一个充满恶魔般愤怒和肮脏忧郁的怪物,在嗜血和忏悔之间徘徊[…] 他热衷于犯罪,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攻击他人或攻击自己” [5]。
齐奥朗认为,历史是西方在面临各种入侵威胁时屈服的重复,正是这种屈服滋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就强迫婚姻背景下的男性强奸问题展开审理 养了俄罗斯的救世主义,使俄罗斯独自屹立于广袤的欧亚草原边境。 “俄罗斯声称要从模糊的主导地位走向彻底的霸权地位,这并非毫无根据。如果西方世界没有阻止和镇压蒙古入侵,会发生什么?在超过两个世纪的屈辱与奴役中,它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而西方国家却任由自己相互撕裂。 » [6]当蒙古人蹂躏草原和中国时,西方基督教攻击了拜占庭,削弱了它,然后抛弃了它,任其覆灭。俄罗斯弥赛亚主义已经接管了东正教。马克思主义重申了这一使命,但并未改变其必要性。“通过神化历史来抹黑上帝,马克思主义只能使上帝变得更加陌生和执着。人类的一切都可以被抑制,除了对绝对事物的需要。 »
齐奥朗对绝对权力的坚信不疑,这促使他宣布,随着俄罗斯获得政治权力,它将抛弃马克思主义,回归宗教。这实际上是这篇文章的科幻方面。 “俄罗斯越强大,就越能意识到自己的根源,而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俄罗斯与自己的根源疏远了;在强制治愈普遍主义之后,它将重新俄罗斯化,以利于正统教义。而且,它给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以至于使马克思主义被奴役了[…]直接源于西方理论的革命,却越来越倾向于斯拉夫派的思想,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 [7 ]值得注意的是,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回应了纳粹对斯拉夫人的蔑视,并激发了斯大林格勒的俄罗斯抵抗力量,最终摧毁了敌人的战争机器。
被奴役人民的力量和自由病毒
当我们西方人看到乌克兰人以模范的力量和活力进行战斗时,齐奥朗的文字再次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帝国内被征服民族的力量。 “[俄罗斯]注定要崛起。可是,她这样急速地攀爬,难道不会冒着失去平衡、摔倒、毁掉自己的风险吗? […]一个帝国越有人性,它内部就会产生越多的矛盾,而帝国最终会走向灭亡” [8 ]
在那里,齐奥朗在东方看到了那些尚未说出最后一句话的被征服民族的活力。 “一些国家,例 WhatsApp 号码 如波兰和匈牙利,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只经历过短暂的崛起[…]。遭受虐待,被剥夺继承权,被迫成为无名烈士,在无助和煽动之间徘徊,他们或许在未来会知道,对他们所遭受的如此多的考验、羞辱,甚至如此多的懦弱,该如何得到补偿[…]。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过于庞大的帝国逐渐衰弱和瓦解,其必然结果是各国人民的解放:哪一个国家将占上风,给欧洲带来这种日益增长的急躁和力量 […]。我毫不怀疑,他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 [9]。他甚至把巴尔干半岛也纳入其中,尽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声名狼藉,而且他已经在罗马尼亚陷入了法西斯主义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