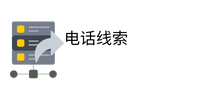一个像燃烧的妓院一样的宇宙,充斥着世界末日、毁灭和内部混乱的味道:这是齐奥朗用绘画铅笔画出来的,他甚至在雅克-阿兰·米勒最近发表的一篇非同寻常的短文《俄罗斯与自由病毒》中加入了苏维埃俄罗斯及其影响下国家的懒惰 [1]。这篇文章写于 1957 年,即红军镇压 1956 年秋季匈牙利革命后不久,但它至今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仿佛作者死而复生,让我们大开眼界。齐奥朗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或小说家,简言之,很难被辨认出来,他摆脱了专家们的常见错误,即忽视了他们所谈论事物的现实性。结果是惊人的,因为他成功地用十几页明亮而清晰的文字阐明了俄罗斯一千年的历史。
他的论点的核心是:俄罗斯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存在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的意义在于超越自己的界限,进行扩张,这种扩张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场危机,更像是一场流行病。她以自己无限的空间为名,为它辩护:“既然我拥有的足够多,为什么不能拥有太多 呢?这就是她的宣言与沉默之间暗含的悖论。”齐奥朗写得一清二楚,他还补充道:她把无限性转化为一个政治范畴,从而颠覆了帝国主义的古典框架 [2]。
这一运动似乎已经消失在
时间的迷雾中,因为齐奥朗让人想起13世纪的蒙古入侵,而俄罗斯在吸收甚至融入蒙古之前阻止了蒙古的入侵。它以一种引人注目且易读的方式重新开始或开始——也就是说,通过与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人的文学主题一起——在 17 世纪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她的情人波将金的推动下,在帝国东部征服了 柬埔寨电话号码库 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斯大林向柏林推进,征服路线转向西方。第一波疫情让我们分心,第二波疫情让我们焦虑。
为了展览的目的而对这些方便的细分做出的保留意见——20 世纪前,向波兰、芬兰等地扩张的运动屡见不鲜——但考虑到这些征服的规模,这些保留意见并不重要。事实上,这并不是按照通常的政治或资本主义逻辑来扩大帝国的问题,而是为了扩大帝国而扩大帝国的问题。这不是普通的殖民主义,不是为致富而进行的偷窃和剥削的混合体,而是一种破坏或蹂躏的方式——俄罗斯“将以肉体的致命性、以其大规模的自动化、以其过剩的生命力压垮欧洲”,齐奥朗写道 [3]。不称霸又能怎样?我们不会称这种扩张为非理性或野蛮的,这只会等于忽视它,但我们会将这 习惯国际法也自动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 种统治欲望视为一种真正的享乐欲望,无缘无故,无缘无故。此外,通过将这种意志置于无限的旗帜之下,齐奥朗表明,这种意志除了自身的力量和与之相反的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的限制:只有当它无法再前进时,它才会停下来。它是一个没有实质的东西(quod without a quid ),一个无法说清它是什么的东西(c’est )。
这将需要暴君的干预
因为如果没有强大的主能指的帮助,享乐就无法将任何人聚集在一起。卡拉姆津是齐奥朗所引述的 19 世纪初第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他认为,专制统治建立了俄罗斯,是俄罗斯存在的基础——斯塔埃尔夫人为了逃避拿破仑这个现代法国唯一允许自己存在的独裁者而逃到俄罗斯,她以更巴黎的风格指出,俄罗斯政府是一种通过绞刑来 WhatsApp 号码 缓和专制统治的政府! [4]历史上从来不乏暴君,从令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着迷的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等不可动摇的偶像。无论他们中有人是更疯狂还是更疯狂,这个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他们如何演奏乐谱,旋律都保持不变。正如齐奥朗所写的:“只有这种对俄罗斯的痴迷才算数。剩下的只是态度。 » [5]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以俄罗斯为思想对象的人们,从最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到果戈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换言之,俄罗斯的某种理念,即“伟大而神圣的俄罗斯”,将差异转化为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