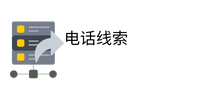由此,蒂姆位记忆,又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这里,记忆是一片片废墟与另一片废墟之间活跃而鲜活的叠加。但多年后再听,我与鲁本的录音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它们经常被其他生活体验打断。我不断听到朋友们热情洋溢的电话,鲁本和他的伙伴们在意第绪语、俄语、德语、英语、希伯来语和波兰语(我后来称之为“生存语”)之间转换,语速难以预测。我还能听到他十几岁的孩子们的进出——轮胎的刺耳声、收音机的震耳欲聋声、背景中的喊叫声和玩笑声。偶尔,一只大型母牧羊犬会带着四只小狗轻快地穿过厨房,鲁本会说自己就像一个幽灵,没有实体,也没有地方可去。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一切生活——朋友、孩子、牧羊犬——以及鲁本的死亡——才是关键。这两个世 WhatsApp 号码数据界无法融合,也不存在更高层次的整合;当下那些关于“创伤”和“韧性”的理论于事无补。人们只需同时抓住两种现实,无需试图整合。埃利·维瑟尔曾写道,幸存者面临的问题与哈姆雷特不同:“生存与毁灭。”
在传统的视频证词形式中
95%的现场,无论具体项目是什么——电话、孩子和牧羊犬都会被彻底封锁——既看不见也听不到。我们最终看到的鲁本,将忽略种族灭绝幸存者最重要的特质——持续的死亡与持续的生命同时发生,同样缺乏综合性。
这又是一个视频证词格式选择和排除最重要的内容的例子。无论你多么仔细地观看同一个幸存者在这种格式下提供多少不同的“证词”,都无关紧要。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即使对于最细心的解读者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无法看到背后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真正知道我们错过了什么。但最糟糕的是,我们很少思考这个问题以及如何改善它。最近关于“边缘”口述历史的研究和对“实践民族志”的需求与此直接相关。但在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的世界里,这样的研究几乎闻所未闻。
这类断言不会受到那些推广和资助视频证词项目的人的欢迎。如果他们有所回应,我们或许会听到一些关于视频证词促成的有价值的项目(我承认确实如此),但我们不会听到更多。除了这些项目之外,还有更广阔的“证词、创伤和记忆”研究领域——其中许多研究受到大屠杀幸存者研究的启发——这些研究也不会轻易放弃。正如沃尔特·本雅明多年前所写,以及我在80年代和最近亚历克斯·弗洛因德所重申的那样,“讲故事”和“生存”的浪漫情怀是难以轻易放弃的。人们已经投入了太多——无论是物质资本、意识形态资本还是政治资本。
我们对习语起源的了解甚至
比对单个单词起源的了解还要少。这很自然:单词有具体的组成部分:词根、后缀、 代理协议的会计处理 辅音、元音等等,而习语则源于习俗、仪式和普遍经验。然而,两者都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并被借用。是谁第一个提出打(或鞭打)一匹愿意跑的马是愚蠢的 新加坡电话列表 行为?又是谁反驳说打死马也同样愚蠢?即使我们找到最早的印刷版引文,或者把这些习语当作所谓的耳熟能详的引语处理掉(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可能创造了其中一句或所描述的幸存者 两句,或者使用了已经流行的短语,从而使它们闻名遐迩),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作者”。过去谁在什么时候死了?谁放荡不羁?为什么只放荡不羁?我偶尔会讨论这些问题。倾盆大雨、巨额赔款、无处可去、鞭打猫,以及其他一些情况都出现在这个博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