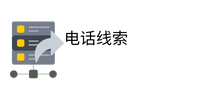从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没有人能够忽视日益严重的当代弊病对学校的影响。然而,学校也是我们被仁慈的话语所安抚的地方,它向我们歌颂着由于人人包容,明天会很幸福,而压抑了我们每个人所遭受的一切 话语之间 。
学校发现自己在“资本主义话语” 与大学话语(简化为神经科学)之间陷入困境,前者“代表了资本主义最成熟、最可怕、最具侵略性和占有欲最强的最后阶段” [1] 。后者致力于制定“和谐共处”的协议,以抑制学生的攻击性,以及其他“诀窍”协议,以 危地马拉电话号码库治疗大脑功能障碍。这两次讲话都应该加上引号,因为不确定它们是否允许社会联系。前者优先考虑驱动力,因为它促使我们通过最短的路径来满足自己;而对于后者来说,根据斯蒂芬·茨威格的公式,学校是“约束、悲伤、无聊的地方,是一个被精确计量地灌输“不值得知道的科学”的地方,学校科目或由学校创造的科目,我们认为这些科目不可能与现实或我们的个人兴趣有丝毫联系” [2]。
学校里的弊病一方面令人沮丧
一方面又让人感到困惑:学生们不再学习,整 天盯着智能手机,只顾自己寻欢作乐,不关心他人;另一方面,人们心中却充满了仇恨。后者在校园内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因此,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他们更多享受对象的奴隶,对于不再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取知识感到厌倦,因此有时会被推向最坏的情况。
为了对抗这种 表现出来的不适感,学术话语诉诸于收集知识来“为所有人” 传播,结合匿名的仁慈和纯粹的知识来压制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攻击性。
一方面学术话语披着康
德式的外衣,辨别善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话语则披着萨德式的华丽外衣。
这种话语交织的结果是,欲望的空间很小,也就是缺乏的空间,从而使对象 移动优先响应策略 的 毒性揭示了 提取变得复杂。从那时起,后者要么位于身体中(正如当代的多动症症状和所有的紊乱或功能障碍所证明的那样) 于另一个中,沦为镜像阶段,由“你或我”引领死亡之舞。